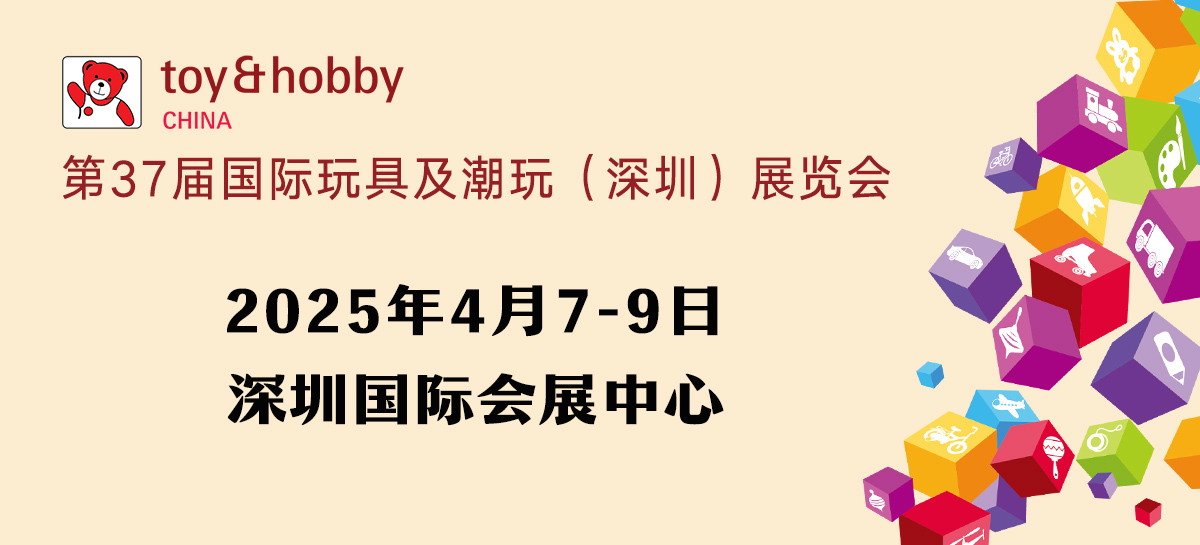Samantha步履轻快地走进教室,她手里端着六套不同颜色的乐高盒子,脸上充满笑意。但教室里的二十个孩子却对她的表情和手里的新鲜玩具无动于衷,像往常一样咬着指甲窃窃私语。
直到她有节奏地晃动起乐高,盒子里的砖块发出清脆的撞击声。眼神涣散的孩子们仿佛瞬间得到了圣诞老人分发礼物的信号,立马骚动起来。

坐在Samantha面前的是二十个眼睛失明的儿童,他们用灵敏手指触碰的玩具也不是普通的乐高。

区别于往常意识中乐高砖块表面均匀的凸起排列,专门为盲童设计的特别版每一个凸点数目都有所不同,代表着盲文字母表的26个字母。

在乐高盲砖中,字母「a」方块就只有左上方的一个凸点,「b」方块的凸点则纵向排列在左侧。老师只需教会每个字母的组合方式,孩子们就能通过组装乐高学会盲文,玩成语接龙写短篇作文了。

盲文的原理与乐高基础砖的凸起设计是不谋而合的。盲文的基本单位是长方形的盲符,有位置固定的六个点,每个点可以凸出或者不凸出,左右两行,上中下三层。对于盲童来说,这六个点就组成了他们的整个世界。
承载着普通人童年所有幻想的乐高砖,如今在盲童的手里成为了他们认知世界的敲门砖。乐高盲块也趁此机会将逐渐衰落的盲文系统保护起来。
在世界的总识字率达到86%的情况下,美国130万的视障人群里却只有10%可以阅读盲文,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还不足3%。因为盲文老师的短缺,学校里的盲童大多是通过有声读物来学习。

盲文书目数量十分有限,一张A4大小的字,也就能写下一两百字,《平凡的世界》译成盲文要用5000多页,三卷书翻译下来就有16000多页。
但盲文意味着读写能力,如果没有这个,“你无法拼写并记忆磁带录音机里播放的内容。”
Orgas从出生起就失明了,她是家里第一个从大学毕业的人,对她来说盲文就是教育的基石。“70%的盲人找不到工作,剩下30%有工作的盲人里,80%有盲文读写能力。”
乐高盲块的出现就是让盲童从玩具本身趋于无限的组合方式中,获取这种能力。

“乐高从来没有迫使我们遵循特定的规则,对于我们想建造什么,不想建造什么,从不设限。”
六块颜色相同的乐高2x4基础颗粒就可以有 915,103,765 种拼砌方式,如同文字的发明一样,给了所有人平等自由表达的无尽可能。

乐高盲砖的项目创意来自巴西的非营利组织Dorina Nowill基金会,目前只发行了300套。他们将这套玩具的设计定义为创作共用授权,任何人都可以基于此进行在创作,以帮助盲童扩大感知。基金会也正在说服玩具行业在全球生产。
对于视力正常的普通孩子来说,乐高最直接的观感是色彩的堆砌,一个个马赛克方块拼成了1080P的高清世界。
而对于盲人来说,他们对乐高的感知来自于凹凸和形状,精度公差仅为0.002毫米的苛刻要求让乐高成为玩具界能给予人类最精准触觉的最高典范,成为感官的延伸。

盲童们能通过摸骨大法以最快速度辨别出来踩到哪一款零件最疼。
面对这个号称可以建造出世间一切万物的玩具,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想象力。很多时候,感官健全的人恰恰才是最容易被局限的那个群体。
同事小陈有次去小区楼下的盲人按摩店,做完推背摸骨全套大保健后,她发现师傅坐在柜台后面低头熟练地玩着iPhone,手速极快。她又想起几天前加师傅微信,看他在朋友圈里转发和家族群亲戚热衷的养生十万加,瞬间觉得这是家黑店,气得摔门而去。

直到有天她在网上看到每一部iPhone都配备无障碍辅助功能的voiceover,可以把所有的交互信息都转成语音,让盲人听到屏幕上的内容。
师傅并不在意小陈的举动,“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能用读屏软件和正常人一样上网,每次我只要一说我是盲人,都会被追问盲人怎么用电脑,说我是骗子。”

被框在以视觉为主导的世界里,普通人永远想象不到上帝在剥夺了人类最主要接受外部信息的方式时,又给盲人们打开了多少通往灵性的捷径。
熟悉代偿效应理论的人都知道,一种劣势会逼出另一种优势,盲人在失去了最主要的感官后,触觉、听觉等都会出现过度补偿,在普通人眼里成为天赋异禀的存在。

在大脑接收外部信息的五大感官中,视觉占据了83%。常人视角里的符号逻辑高度依赖于视觉,虽然触觉同样也能代替。不过视觉信号带宽大,触觉带宽小,如果只通过触觉来建构物理世界,就跟拿猫拨号看高清大片没什么区别,这属于开挂玩家,惹不起。
给小陈按摩的师傅最喜欢“看”手机里的Kindle,在选取了一段文字后,叽里咕噜的语音让小陈以为是在接收异星信号,那实际上是加快若干倍后的速读文本。师傅不但能听懂,还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和拼写,这是盲人求知欲驱动下锤炼出来的能力。
不只是听觉,在触觉感官上,对于平时连麻将都摸不透的普通人来说,盲文的触感就像胳膊上凸起来的鸡皮,除了想把它们抠掉之外,解读不出任何信息。
而盲人不光能精准感知每一个凸点的位置,还能记住它们的镜像形态。

盲人写盲文时,从右到左,阅读时,把纸翻过来,从左到右摸。这就要求学习盲文的人不仅要学习每个盲文字母的正常形态,还要记住它们的镜像形态。
除此之外能用它来编程写代码,变幻出如同乐高一样无尽的可能性。

Jordyn Castor是一名在苹果工作的盲人女性工程师。她用数字Braille和字母Braille来书写代码。另一位盲人程序员蔡勇斌用“背”代码来编程,最多的时候背过300多行代码。他们的双手就像USB3.0的接口,极速接收并解读着信息。
有些盲人甚至练就了海豚和蝙蝠的天赋,可以利用回声定位的特殊视物方法来判定周边物体大小、形状甚至纹理的信息。
埃里克·魏迈尔在13岁时因为遗传病双目失明,但他却依靠背上系的响铃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利用铃声的回响,拄着盲人爬山手杖沿着路标爬行。接近珠峰时,埃里克彰显了他作为盲人的优势,他不必带护目镜也不用借助矿灯摸索行进,最终征服了世界之巅。

普通人看东西是有边界的,而对于盲人来说,视角是180度的,这种视觉理解塑造了他们比普通人更能辨别环境模式。
劣势和优势不是绝对的,往往依赖于外部的环境。不是所有盲人都爱唱你是我的眼,如果在黑暗中来一场乐高组装大赛,身为普通人的你可能连一个基座都拼不健全。
“下班路上看到一个盲人拄着拐杖在大街上走,不疾不徐,神态淡然。他可以在人流里完美躲避迎面而来或者后面抢道的行人,仙风道骨地像个世外高人。”
面对被各种缘由霸占的盲道,普通人在网上抱怨这是形象工程,而盲人的棍子总能感觉出来,玩手机不看路的明眼人才需要当心。

这些地面上凸起的盲砖,像乐高零件一样被随意地拆卸、挪动。
失明并不能定义什么,看见与否也只是基于感官的认知。有人在明晰的世界里一叶障目,有人却在混沌的黑暗中得到光明。
你也许觉得有人出厂就是低配设置,但至少他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乐高。比起思考无可挽回的不公平性,他们更愿意有尊严地享受当下的快乐。
愿他们最后将乐高拼接成功的刹那,有着侠客收剑入鞘的骄傲。

“我知道帝国大厦长什么样子,我用乐高建造过它!”